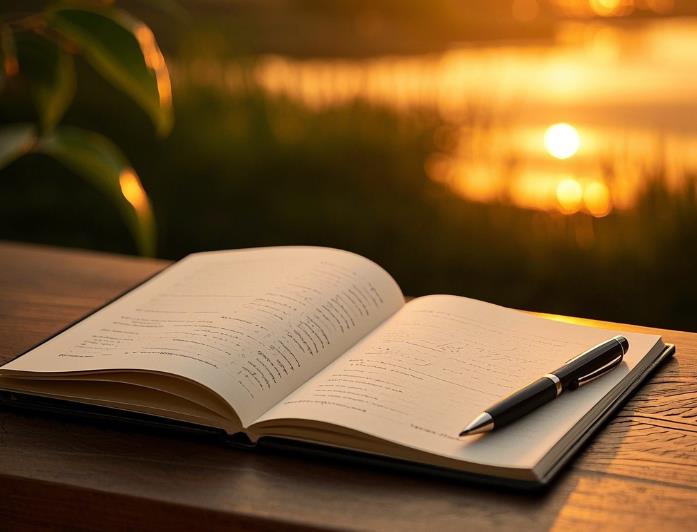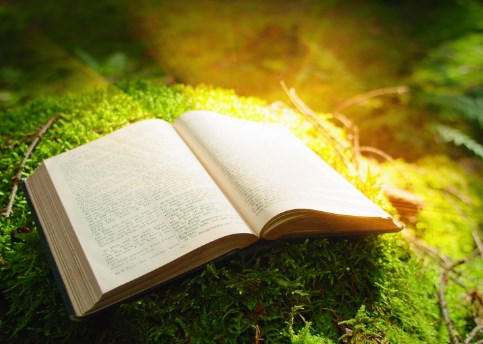郭进拴|六十岁说【二百九十八】
来源:会员中心
作者:2855510
发表于: 2025-04-13 08:38
郭进拴|六十岁说【二百九十八】
随后,又来了,1992年早春,方友寄来一个长长的成绩单,还说是要目。我在此不一一列举,大体上,中篇十几部,短篇数十篇,小小说上百篇,一百二十余万字。他在附信中夸我的眼睛,说我在十二年前的1980年第一眼看他时的眼神就充满自信,自信没看错人,云云。并请我为他写篇文章评说评说。我看了方友那成绩单,高兴,我看那附信,就想笑,这哪里是夸我,分明是拐着弯儿夸自己啊。文章我写了,大约是较早评说方友的文字,题为《晕说孙方友》,文章的开头我就说:
“据说十二年前我第一眼看方友的目光叫方友难忘,据说我那目光非常自信,自信没看错人。当我看到方友寄来的洋洋洒洒的作品要目时,就很为自己十二年前的那目光骄傲,就很想回忆那目光,只可惜自己的目光自己看不到,回忆就发生了困难。虽然难于真切地回忆起那目光,看着眼前这要目的洋洋洒洒,也如同喝了杯新毛尖茶那般滋润了。……”可以看到我情不自禁地对方友的赞赏之情。
1992年,我与方友大约有一次见面,方友在《南丁印象》中如此描述:“由于我去年(1992)身体欠佳,南丁先生离职之后我只见过他一面。在省文联小招待所,他去看望作代会代表,306房间,他握住了我的手,目光慈祥,平和而善良,打量许久才说,‘要力作!’话仍然低沉凝重且残留着主席风度。”方友在同一篇文章中两次提到我的目光,重复用了慈祥平和善良这个词,我自己不知道是否如此,因为我看不到我自己的目光。还说起我的风度,还是主席的,且残留着。我还有风度吗?有意思。小说家孙方友这里用的手法是写实还是浪漫呀?
1993年末,我应邀为“颍河作家丛书”写总序,在那总序中我写到:“于是就顺理成章地生长出这套‘颍河作家丛书’来。这个阵势中写小说的挺红火热闹的孙氏兄弟方友、墨白,写诗的梁辛,搞评论的李少咏,是熟识的,其他各位朋友则暂未谋面。第一辑即推出十二本,也够浩荡。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阵势中的一部分,这只是他们作品中的一部分。”“搞文学的企求什么呢?自己的作品,如能像颍河水里的波浪中的一滴滋润过了什么,如能像颍河平原上的春风中的一缕吹拂过了什么,也就得到欣喜和安慰了吧。”“倒真的不必夹着尾巴作文。说不定也有人会弄出更大的气候来,走向不朽,与永恒奔流不息的颍河共存。那就让颍河作证吧。”这最后一段文字,是期待也是预言。“说不定也有人”是暗指,颍河作家群中人会看的明白,那是指孙氏兄弟的大哥孙方友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吧,方友被借调至河南省文化厅属下的《传奇故事》编辑部工作,编辑部报请文化厅拟正式调入,数年过去仍无消息。方友着急,拿着两条红塔山香烟(未能免俗啊)来找我求计求助。我不是为那两条红塔山(我日常吸烟的品味要比此略高些),我只为了方友那两只无助的渴盼的眼睛。我当即爽快答应,此事我来办。就好像此事就归你管,我只一句话就可办成事。其时,我早已离开文联的领导岗位,但我与文化厅长是可以说话还谈得来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厅长政务繁忙忽略了此事,也可能是因为对方友了解不多,导致对这个难得人材的价值认识不足,我要亲自去向他游说推荐,我相信他会听取我的意见的,我信心满满把握十足。那天上午送走方友后,我随即骑了辆自行车直奔文化厅,那时文化厅还在花园路那老地方,经七路往南左拐纬一路往东至花园路,十几分钟就到了,我爬上四楼,就找到了正在开会的文化厅长,我把他拉了出来,坐在外间,说了此事,他仔细倾听并用笔记下。不久,1997年10月,孙方友正式调入《传奇故事》编辑部,户口也随着转入郑州。一切顺利。此后,方友老将此事挂在嘴上,说我对他有知遇之恩,真不敢当。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本网站所有。凡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本网站”。
上一篇
郭进拴|六十岁说【二百九十七】下一篇
郭进拴|六十岁说【二百九十九】分享到:
作品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