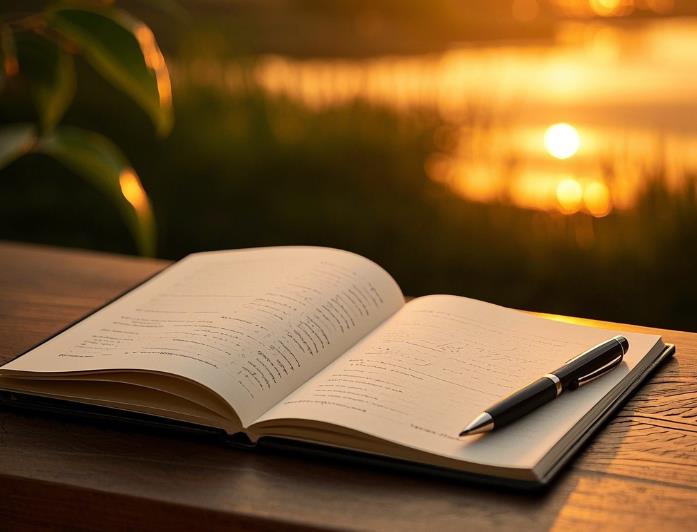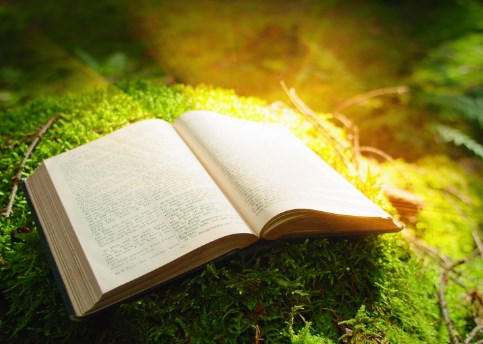郭进拴|六十岁说【三百】
来源:会员中心
作者:2855510
发表于: 2025-04-13 08:40
郭进拴|六十岁说【三百】
2014年7月26日的孙方友小说全集(二十卷)前八卷《陈州笔记》《小镇人物》首发式暨孙方友逝世周年纪念会上,方友的女儿孙青瑜送我一本书,作家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的孙方友著《小镇奇人》,计六十三篇,二十八万字,为小镇人物的精编本,说是为方友生前亲自编定。书的封面和扉页用了我一句话:“孙方友的新笔记体小说要传世,他是当代伟大的小说家。”这句话,为我在2013年8月9日方友的追思会上所说,作家出版社在报刊上摘了我这句话作为广告词。能为方友的小说的推广做点事说句话,我感到高兴和荣幸。
我所以如此说,不是感情用事,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哗众取宠,是有着方友的创作实绩作为依据的,坚实的依据。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孙方友小说全集》,已先推出他新笔记体小说《陈州笔记》《小镇人物》计八卷,将要陆续出版的为中篇小说三卷《虚幻构成》(1985——1991)、《血色辐射》(1992——1995)、《都市谎言》(1996——2011),短篇小说二卷《黄色的雾幔》。
大家都说,河南文学的盛世,真正的奠基人就是何南丁先生。南丁先生的作品有黄河荡气回肠的磅礴与大气,有跨越数千年的文史积淀作内涵,有中原大地的厚重、带着中华文明的灵性。笔者没想到,何南丁先生的言谈是简明扼要的。凡与人交谈,他能三言两语就讲明的,不再多说。先生不爱长谈,在他身上找不到居功自傲、颐指气使之感。这位全国一级作家,总是让人觉得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为何?无外乎他由内至外流露出的良好修养。就是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人,当年以他为代表的河南作家群凭着强劲的创作势头,取得了不凡的成就,让人看到豫军在文学界的崛起。何南丁先生很谦虚,一直说乔典运、张一弓、李佩甫、田中禾等人都是文学豫军中的顶梁柱。南丁先生认为,豫军在中国文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代文人袁枚说过:“诗得一字之师,如红炉点雪,乐不可言。”笔者曾与何南丁先生谈话,偶然提及一件事情,他马上会微微一笑地讲,若是能够朝着那个方面发展,就是一篇小小说的好素材。所以,或许只是通过先生一个友好的微笑、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知心的话,却总能让人感受到他的涵养与睿智,还有才思的敏捷。何南丁先生正是凭着超人的才华与内涵打动他人。
南丁先生谈道:“当年《河南日报》社曾经设在开封一段时间,我就是在那时当的编辑。”他1949年结业于华东新闻学院,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检验工叶英》《在海上》《被告》,中短篇小说集《尾巴》,散文随笔集《水印》《南丁文选》《南丁文集》(五卷)等。他有分量的作品虽多,但并不显得冗长,都是显得那么恰如其分。那次我问到南丁先生的女儿、同样是德艺双馨艺术家、从事文艺理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何向阳时,老先生和蔼地问怎么知道他们是父女,怎么知道女儿的情况。这次,我笑了,答道,喜欢文学的人总会知道你们父女,在报刊上见过相关文章,知道何向阳擅长评论,原来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当过河南大学特聘教授、省作协副主席,获得过冰心文学奖,现在中国作协工作。总之,这父女俩是河南文学界的骄傲。何南丁先生告诉笔者,当初并未刻意培养女儿从事文学创作,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女儿还是踏上这条路,并且坚定地走下去。
虽然到省里工作多年,但是何南丁先生怀着深厚的感情多次回到开封和兰考,有时是为了采风,有时只是为了品尝开封夜市小吃,在这个七朝古都的街头走一走,回想一下在汴工作时的青春岁月,再细细打量着日新月异的城乡面貌。这一切一切的深情,都在先生的笔下流淌,他先后写下3篇和兰考有关的文章,其中不乏思辨性,分别在《河南日报》、《随笔》、《奔流》上发表。先生对文学创作的关注与支持,大家有目共睹。
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时,该馆馆长邀请何南丁先生写句话留念,老先生略一思索,提笔写下:“人之光荣”。在参观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处后,何南丁先生安静地坐在河边石桩上休息,参加笔会的作家们纷纷要求与他合影,先生微笑着一一点头答应,没有一丝厌烦。
那天晚上,采风作家联欢,南丁先生不仅带头唱了几首带着异域风情的俄罗斯民歌和我国的红歌,还风度翩翩地跳起交谊舞,歌声动听,舞姿潇洒,展示出80多岁老人的魅力,真让人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大家一次次地鼓掌叫好。有年轻作家要求与人合唱王菲版本《传奇》时,南丁先生踊跃地接过话筒,颇有感觉地引吭高歌。这更加博得大家阵阵欢笑声。
南丁先生常说:“不要有功利之心,坚持、真正热爱,多阅读经典名著,保持创作激情,保持从内心喷涌而出的炽热的创作状态。”这就是何南丁先生,一位德艺双馨的名家风采。
南丁在《李佩甫和他的小说》一文中这样写道:
李佩甫写小说已经十年。起步时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在中原这一群年轻的作家当中,并未引人注意。他朴实诚恳,谦逊好学,倒是块做编辑的好材料,就调至《莽原》编辑部工作。一面工作,既要读大量未印成铅字的原稿,又要读大量已印成铅字的中外古今多个流派的作品;一面学习,上电大啃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以补偿历史对他的亏;一面仍坚持业余小说创作。三面出击,也够苦的了。好在年轻气盛,各方面都还令人称道。
这期间,读到他的《蛐蛐》,与他起步时的虽有真情但总显拘谨的习作相比,就颇有点儿灵气儿,就觉得对这个李佩甫应当另眼相看了。后来,又读到他的《森林》,是在宣泄一种男儿的阳刚之气,分明是他的自我宣泄,那粗犷,也不是用糨糊粘上去的。我就猜想,他要有一点儿大的动作出手。别看他不吭不哈,寡言少语,却有心计,有大志,内秀呢。我注意到他对同辈写作的朋友不卑不亢,学人家的长处,不嚼人家的馍。总会有名堂。《红蚂蚱、绿蚂蚱》,证实了我的猜想,果然出手不凡。这篇三万余字韵致别具的小说,文体学家也说不清楚它的归属,是中篇小说,还是系列短篇小说呢?这好像也不是无关紧要,留给文体学家去研讨吧。十小节,十个人物命运的片断。真切生动地塑造了“住着姥姥的村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形象。深沉,凝重。
这也有来由。佩甫与农民一起背过日头,与工人一起开过机器。他懂得生活的艰辛、创造的艰辛。经年累月,生活与创造赐予了他深沉凝重的气质。他的气质给了他的小说深沉凝重的调子。他总是写正剧,好像缺乏幽默感。比如《红蚂蚱、绿蚂蚱》中的《选举》,如此荒诞的事件,闹剧、喜剧,都可大做其文章,他却选择了正剧的写法,全是白描,毫不渲染,这就给读者留下再创造的极大的空白,读来或叫人心眼发酸,或叫人笑得发晕。近乎噱头的廉价的幽默,当然要失之于浅薄,还是不要的好。
与佩甫共事几年,又同住一个大院,个人交往却不多。他偶尔来家坐,却不善谈吐,如同他写小说,极凝练,说完了就走,好像怕耽搁我的时间。有次谈起写小说,他自言自语说自己:“思想不能掉下来。”这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如今的年轻人,如此说的不多,即使说,也要换一种说法,说一些玄乎得叫人费解的新词。佩甫却还说这种老话,叫我吃惊。《红蚂蚱、绿蚂蚱》之后,又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的十七代玄孙》问世,现实与历史交错叠印,纵横捭阖,游刃自如,很有点儿大家子气了。
他近年来家几次小坐,话题是希望能给他时间从事专业创作。说是几年的编辑工作确实给了他许多不可替代的补益,但当前有几个东西想写,按捺不住冲动,需要整块的时间,以后如需要,还可重做编辑工作。话依旧不多,却很执着。想起他在《森林》中宣泄的男儿气,那不是用糨糊粘上去的粗犷,想起《红蚂蚱、绿蚂蚱》和《李氏家族的十七代玄孙》,有些相信他终会成大器,势头又正旺,就觉得延误了这位人才的黄金时间,也是罪过,也就未敢不同意。
从事专业创作后,他件事就是冒着寒风回到他插过队的村子里(是“住着姥姥的村子”吗?),去寻找感觉,强化情绪。这种寻找,这种强化,我记忆中,他不时插空进行,他在实践着另一句未说出的老话:“生活不能浮上来。”老话大约也不必一概打倒吧。开放,打开窗读现代主义的作品,闭紧门拒绝涌动的现实生活,总不能算是完整的开放。两个不能,恐怕也不仅是为文之道。
佩甫要出小说集,叫我写序,这大约是一年前的事,于是,便找来小说,一一看过。看过后,就搁置在那里,又忙乎别的事情去。一搁置,就经年。催过几次,我很有些不好意思。近又说集子早已编好,就等着序一起发稿。我也就愈加歉然。乘着龙年春节假日,胡涂乱抹,冒充序言,未知可否蒙混过关。
南丁先生不愧是文学豫军的栽树人!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本网站所有。凡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本网站”。
上一篇
郭进拴|六十岁说【二百九十九】下一篇
郭进拴|闪光的足迹【八十一】分享到:
作品赏析